


【嘉 賓】 伍 江
同濟大學副校長 張 松
同濟大學城市規(guī)劃系教授、博導
主持人的話▲▲
北京市文物局和東城區(qū)政府近日通報,梁林舊居被拆是破壞古都文物保護的一起惡劣事件,目前依法對開發(fā)單位及有關(guān)責任人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同時責令其恢復所拆除舊居建筑原狀。這一事件讓老建筑保護的話題再一次被熱議,那些令人擔憂的空白和誤區(qū)也隨之浮出水面。
“梁林故居”的價值 在于其承載的歷史和記憶
主持人:“梁林故居”被拆,引起了公眾的憤怒。我們?nèi)绾谓庾x這種憤怒?
伍江: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的建筑是北京傳統(tǒng)的四合院,就如同上海的石庫門。也許單單作為四合院來看,它未必是最有建筑藝術(shù)或技術(shù)價值的。但是,在這個四合院里曾經(jīng)居住著特殊的人,發(fā)生過特殊的故事,就好比上海的一大會址,那棟石庫門房子從建筑的角度看,也許不是上海最好的石庫門,但在那里發(fā)生過改變歷史的事情,使得這棟建筑有了重要的文化烙印和重大的歷史記憶,這些是無法復制替代的。“梁林故居”曾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居所,也因為他們的緣故,這里曾經(jīng)成為了文化名人聚會的場所,這座建筑承載了許多的故事和記憶。這是其作為名人故居的價值所在。
對“梁林故居”被拆的憤怒,反映出這幾年來大眾保護文物的意識提高了。此外,還有很重要的原因,梁思成、林徽因作為中國古建筑保護事業(yè)的先驅(qū),梁思成是最早提出北京城整體保護提案的人,他的方案當時沒受到重視,后又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這樣的時候拆他的故居,更讓公眾覺得難以接受。
主持人:在媒體報道中,我們獲悉,梁林故居2009年的時候就差點被拆了?
張松:是的。2009年時,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內(nèi)的北總布胡同要拆遷,新華社高級記者王軍接連發(fā)表三篇文章,呼吁“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北京引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拆”與“留”的大論戰(zhàn)。最終,北京市文物局會同市規(guī)劃委責成建設(shè)單位調(diào)整建設(shè)方案,在建設(shè)規(guī)劃上確保故居院落得以保留,同時表示,清華大學新林院8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將得到保護。
大量文物沒等到“法定身份” 完善配套制度迫在眉睫
主持人:我們注意到,被拆的“梁林故居”,之前已經(jīng)被列入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發(fā)現(xiàn)項目,確定為登記不可移動文物。可是,拆房子的單位卻說自己的行為并不違法。這是為什么?
伍江:中國《文物法》針對各級文物保護單位,文物保護系統(tǒng)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公布過幾批,數(shù)量非常有限。實際上大量文物并沒有確立合法的保護地位。近年國家組織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找到了幾十萬處文物,但現(xiàn)在沒有條件將這么大數(shù)量的文物都列入文物保護單位名錄。于是《文物法》還規(guī)定了一個先行登記的措施,這就是“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的由來。“梁林故居”已被列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這樣做的初衷當然是希望之后能將其列入文物保護單位。
開發(fā)商的行為是在鉆法律的空子。在現(xiàn)有的法律中,沒有針對破壞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的懲罰措施。這就意味著,開發(fā)商在其尚未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時將其拆除比較合算——即使受到處罰,罰得也比較輕。但是,沒有違法就可以做壞事嗎?“梁林故居”被拆的這個事情中,我們要吸取教訓,盡快完善法制,提高全社會對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意識。
上海前些年由市政府批準實施的“歷史文化風貌區(qū)保護規(guī)劃”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保留歷史建筑”的概念,就是試圖通過法定規(guī)劃來“凍結(jié)”一大批具有一定歷史文化價值但又暫時無法列進保護名單的歷史建筑免予拆除。這一做法保護了一大批歷史建筑免遭于難,但也由于缺少相應(yīng)的法律配套,還是不斷有“保留建筑”被拆除。政府對“保留歷史建筑”被拆后的處罰手段也顯得非常乏力。前幾年發(fā)生在原圣瑪麗亞女中舊址上的幾座保留歷史建筑被拆除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因為屬“保留歷史建筑”,拆了也就拆了,并無有足夠威懾力的處罰。還有提籃橋附近的猶太人白馬咖啡廳被拆事件,阮儀三教授曾為此發(fā)出保護呼吁,之后有關(guān)領(lǐng)導也做了批示。可是,幾個月后,那個咖啡廳還是不見了。因為屬“保留歷史建筑”,也無嚴格的禁止拆除的法律規(guī)定,說是為了拓寬道路不得已拆除,可實際上這座建筑并不影響道路拓寬后的交通,只是放在那里影響了道路的“美觀”罷了。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對于“保留歷史建筑”制定有效的保護措施已勢在必行。
落架維修是托詞 原樣修復存誤區(qū)
主持人:這次我們還聽到了一個說法“維護性拆除”。這個解釋成立嗎?
伍江:“維護性拆除”的說法,就如同“殺死性治療”的說法一樣荒謬。開發(fā)商那么說,是他們不懂。不過,我們也聽到了主管部門的解釋,說是對“梁林故居”進行“落架維修”。這是個很專業(yè)的名詞,但是卻被用來描述了一個不對的事情。混淆了普通百姓的視聽。我們說的落架維修,是針對中國古代木結(jié)構(gòu)建筑的一種特殊維修方法。在“落架維修”中,老舊的房屋構(gòu)建被小心拆卸下來,清理維修后,重新原樣搭建(古代木結(jié)構(gòu)的房屋各個結(jié)構(gòu)之間的連接主要都靠榫頭,因此使得這種方法非常簡單),這個過程中,房屋原來使用的材料和工藝都沒有變,每個部件也都在原來的位置。對于現(xiàn)代的磚石結(jié)構(gòu)的房子,事實上很難做到真正的落架維修,必須做到對每一個構(gòu)件和每一塊磚石都編號,保證它在重新砌起來的時候還在原來的位置。而且,在這個事件中,最后還露出了狐貍尾巴——相關(guān)部門稱,將請有專業(yè)資質(zhì)的單位來進行復原設(shè)計。如果真的是按照落架維修的要求做,何須另外找公司進行復原設(shè)計?如果“梁林故居”真的是危房,那就應(yīng)該早早地請有專業(yè)資質(zhì)的文物保護機構(gòu)來進行維修,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拆除。
主持人:有關(guān)部門說,考慮原樣復建,再造個一樣的。從專業(yè)的角度看,這樣做合適嗎?
張松:建筑、院落都拆完了,按文物法相關(guān)規(guī)定就不要再重建了。保持現(xiàn)在的殘破面貌,然后在旁邊立一個碑,把這個地方的前世今生記錄一下,告訴后人,這里曾經(jīng)有過什么故事,后來怎么被拆的,讓后人知道我們當年是如何犯傻的就可以了。
伍江:在對老建筑的保護中,有不少人持有這樣一種觀點——房子老了,拆掉重新蓋一個一樣。要知道,建筑帶有文化信息和烙印。按原樣造個假的,文化信息就沒有了。這就是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強調(diào)“原真性”的原因所在。令人擔憂的是,在老建筑保護的工作中,有不少人,特別是不少政府官員,對于所謂的“原樣修復”的做法還是認同的。
張松:最近五六年來,保護性破壞的情況時有發(fā)生,令人擔憂。所謂保護性破壞,就是以保護的名義修繕,或者拆了重建。譬如北京中軸線,它是古代城市建筑中最輝煌的一個空間秩序。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有一些局部的改建,總體上看,做得還不錯,高度、景觀控制都還行。可是,現(xiàn)在聽說當?shù)匾环矫嫦胍獙⒅休S線申遺,一方面卻在計劃將那一帶原有的四合院等建筑拆掉,蓋仿古風貌的新建筑。我覺得相關(guān)部門一定要想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文化遺產(chǎn)保護。對于文化遺產(chǎn)保護,有《世界遺產(chǎn)公約》和相關(guān)國際憲章文件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而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則是文化遺產(chǎn)保護最為關(guān)鍵的因素,文物古跡首先應(yīng)該是真的,周邊環(huán)境應(yīng)該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整體。拆了舊的重新造新的,或者留下孤零零的一個老建筑,將周邊環(huán)境都改造甚至破壞了,都是違背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基本原則的。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不能功利心太強
主持人:“梁林故居”的事情讓我們不禁聯(lián)想到其他更多的需要保護的老建筑。上海的名人故居保護情況如何?
伍江:目前在上海,從政府到開發(fā)商,對于老建筑的保護總體而言還是相當重視的。有的區(qū)針對名人故居保護還專門建立了很有效的管理機制。不過,還有很多名人故居沒有被發(fā)現(xiàn),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展開。有一點要特別提到的是,大家現(xiàn)在看到的很多名人故居,建筑本身的狀況還比較好,在保護問題上難度不大。如果建筑本身的狀況不佳,屬于危房,是否會遭遇到“梁林故居”的命運,還很難說。
我們會遇到這樣的一種情況,一些狀況還不錯的名人故居,比如巴金故居,修繕后作為巴金紀念館,大家都意見一致。但是,一提到保護石庫門,就會有爭論。覺得很多石庫門房子太破舊了,沒有保護價值。但是,老建筑是否值得保護,不是看它的外表好看還是破爛。難道能因為媽媽長得丑就不要媽媽?
主持人:有時候我們不禁要問,我們保護老建筑,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到底是為了什么?
張松:現(xiàn)在很多地方的保護項目多是出于功利目標的。沒有經(jīng)濟價值就不保護。保護下來的那些,相當部分都是為了開發(fā)旅游和所謂的文化地產(chǎn)。
要知道土地不只有經(jīng)濟效益,還有生態(tài)效益、景觀效益、社會效益、文化效益等等,文物不只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實物,還應(yīng)包括任何具有文化意義的物質(zhì)形態(tài)——城市空間、生活場所、歷史環(huán)境。北京、上海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我們保護這些老建筑,和我們現(xiàn)在大力提倡的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打造宜居城市等等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地方政府既要在宏觀政策上高度重視,又要在具體行動上真正做到創(chuàng)新驅(qū)動。
借鑒國外模式將老建筑發(fā)揮保障房功能
主持人:國外在老建筑保護方面是怎么做的?有沒有可以讓我們借鑒的地方?
張松: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歷的這個階段,歐洲也曾經(jīng)歷過。但他們的時間比較短,造成的破壞也就沒有那么嚴重。保護的早期,歐洲對老建筑的保護也著眼于“帝王將相”的房屋,但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歐洲開始保護老街區(qū)——即開始重視保留老百姓的歷史。這些平民居住的老房子記錄的是公眾的歷史,是區(qū)域社會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它們是具有識別性的場所。現(xiàn)代社會中,很多城市都面臨著特色危機,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也隔斷了過去的社會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很多人懷念老式里弄里,人與人之間親密的關(guān)系,我們保留下這些老建筑,也是留下城市的歷史痕跡和市民的生活記憶。
老舊房屋需要花錢修繕維護,歐洲的做法是會給予房屋的居住者50%的補貼。美國則是會在個人所得稅上給予優(yōu)惠。在歐美,還有另一種方式,政府將老建筑的產(chǎn)權(quán)買下來,進行維修改善后,作為類似我們的保障性住房,租給低收入者或?qū)W生。這種方式很值得我們借鑒。
以上海為例,這些年來,新蓋的房子使得城市用地蔓延過大。與此同時,在市區(qū)還有大量的里弄住宅等老建筑。一方面,老弄堂重生需要資本投入、外觀修繕,但最重要和最為基本的在于原住居民的環(huán)境條件改善與生活狀態(tài)延續(xù)。另一方面,即使原居民不愿在這里繼續(xù)居住,這些老建筑產(chǎn)權(quán)大多在國家或地方政府手里,如果政府花錢進行適當?shù)恼胃脑欤鳛楸U闲宰》俊⒐夥刻峁┙o低收入人群居住,那將是雙贏的事情——改造老房子花費不會比到郊區(qū)蓋新房子更貴,而低收入者也不必煩惱住在郊區(qū)給工作生活帶來的不便。
▲▲結(jié)束語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是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題。“梁林故居”的命運,讓我們看到完善相關(guān)法規(guī)制度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認識到保護和利用的辯證關(guān)系。更重要的可能是提高全民意識,自下而上地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
行業(yè)領(lǐng)域招聘 首選行域人才
版權(quán)所有: 行域人才網(wǎng) copyright@2003-2023 http://www.mthcjy.cn all rights reserved
粵ICP備11096293號-1 行域人才網(wǎng) 人才網(wǎng)聯(lián) 專業(yè)人才網(wǎng)
一覽英才網(wǎng) 深圳市行域信息技術(shù)有限公司 版權(quán)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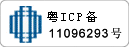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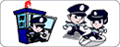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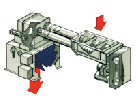 打印]
打印]
 收藏]
收藏]
 關(guān)閉]
關(guān)閉]
 返回頻道]
返回頻道]


